“第一次聽說 Neuralink 之后僅僅六周,我就確定其工程之大膽、使命之壯麗,簡直讓特斯拉和 SpaceX 都黯然失色。那兩家公司在試圖定義未來人類會做什么,Neuralink 則意在定義未來人類是什么。”
這是著名科技作家 Tim Urban 在 WaitButWhy 上發表長文的一段話。這篇文章詳解了 Elon Musk “腦機接口”的前世今生和 Neuralink 的宏偉藍圖,包含大腦研究的深入介紹。
Elon Musk 表示, 超級人工智能必將實現,人類只有一個選擇:成為 AI。他認為腦機融合后的 AI 系統將以和人類的本能大腦與理性大腦同樣的特性存在。人腦和計算機將融合無間,人類甚至無法察覺自己在運用 AI 思考。
今天的文章分享雖然有些長,但全文貫穿著搞笑而又邏輯清晰的圖片,文風也是 Urban 一貫深入淺出的風趣幽默,希望對你有所啟發。以下,Enjoy:
一、人類只有一個選擇:成為 AI——Elon 的宏圖
很多情況下,鋌而走險以爭取最好的結果不失為好的策略,但是當賭注過高時,還是謹慎行事為妙。權利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么,Elon 視 AI 為終極的權利,因而也認為其發展尤其需要采取謹慎的態度。他所持的,最大程度降低 AI 對人類威脅的策略基本就是這個意思。
為了在 AI 領域推行這一理念,Elon 從不同角度做出了多種努力。
他和 Sam Altman 創立了 OpenAI,自述為“一家非營利性的 AI 研究企業,致力于研發和制定實現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的路徑”。
通常情況下,當人類創造新事物時,總是由一些具有創新意識的先行者引領。嘗試成功后,隨著一個產業的誕生,那些企業的巨鱷會參與進來并將先行者的努力全面發展壯大。
但是,如果那些先行者制造的是一根魔杖,這根魔杖會賦予掌握它的人無上的,堅不可摧的,凌駕于所有人之上的權利,甚至阻止任何其他人再制造魔杖的權利。這就有點兒棘手了,對嗎?
Elon 眼中今日 AI 發展的方向就是上面這種情形。既然無法阻止人類創造魔杖,他的解決方案就是創造一個開放、合作、透明的魔杖研發實驗室。每當這個實驗室中產生了新的研究突破,不同于其他會將此視為秘密嚴守的公司,他們會將這一突破公布給所有人去了解,或借鑒用于各自的研發。
一方面來講,這么做也是有明顯的缺點。邪惡勢力也在努力制造魔杖,誰也不想第一根魔杖是從他們手中誕生。如今,壞人們的研究也能從這一實驗室的創新成就中獲益。著實令人擔憂。
但是這一實驗室也促進了成千上萬其他人的研究,并對早期的小部分先驅者形成了巨大的競爭。一些人大幅先于其他人制造出魔杖已無可能。比較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當第一根真正意義上的魔杖最終被制造出來時,已經有成千上萬類似的成品同時存在,即具備不同能力,被不同的人所創造,多種用途的其他魔杖。
如果地球上要誕生魔杖,Elon 認為,至少讓它掌握在全球的大部分人而非一位握有極權的魔法師手中。他自己這樣表述:如果每個人都來自氪星球,那沒什么問題了。但是如果只有一個超人,而這個超人還希特勒附體,麻煩就大了。更糟的情況是,某一位先行者的魔杖很可能是基于他滿足自身的需求創造的。如若將未來的魔杖產業發展為集體智慧的結果,多種多樣的需求和目的都應該有對應的魔杖去滿足。應該使得全世界魔杖的能力都是首先反映了大眾的需求。
尼科拉·特斯拉、亨利·福特,萊特兄弟和阿倫·圖靈都一馬當先引領了產業革命,這都沒問題。但是當被創造的東西將擁有無法想象的極權時,我們不能袖手旁觀,風險將難以掌控。
Elon 總結道:AI 必將大幅超越人類的能力。為了讓它的存在與人類,尤其是絕大多數人類共同的意愿相連接,它應該是基于大多數人意愿產生的結果,因為它將服務于這些人的意愿。
剩下的就是“民有”部分。
這部分解決起來應該比較容易。別忘了那些產業巨頭正在基于他們制造汽車、大型機械和計算機的同一個目的——創造超級智能 AI,即拓展他們的疆域,并將其中將產生的工作外包。汽車是代步工具,大型機械是制造工具,而計算機解決了信息存儲、管理及計算的問題。具有思考能力的計算機將是偉大的創造,它能使得人類將最重要及最高強度的工作實現外包。人類的一切都構建與思考之上,想象一下制造一個人類思考能力延伸的超級智能所將帶來的巨大能量吧。而人類的延伸從定義上講也屬于人類,即“民有”。
只有一個問題:具有超級能力的 AI 不同于其他發明。其他的技術都擅長于它們自身的制造用途,但總的來說,它們僅僅是些具有非常有限智能的無意識的機器。但我們現在試圖制造的 AI 將像人類一樣聰明,且超級聰明。同樣的規則怎么還可能適用?
人類自己創造的技術當然是屬于人類的,這一觀點如此顯而易見,說出來都顯得有點兒傻。但是如果我們創造了比我們自己還聰明的事物,它還能那么容易被控制嗎?
有沒有這種可能,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事物,其智能高于任何人類,將不滿足于僅作為人類的附庸而存在,即便它被制造的目的如此?
我們無法預知實現的場景,但保險的做法是現在承認,是的,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擔心變為現實,我們的麻煩就大了。
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地球上一旦出現智能遠高于其他物種的物種,它必將對其他所有物種構成威脅。如果 AI 變成了這樣一個最高智能物種,而它又不屬于人類,它具有自我意識,那我們人類就被歸入“其他所有物種”的類別了。
因而壟斷 AI 就是問題所在,OpenAI 就致力于解決這一問題。但與之相比,更嚴峻的問題在于防范 AI 失控。
Elon 為此輾轉反側。在他看來,超級智能 AI 的崛起只是時間問題,在那一天到來之前,人類務必要避免自己不落入“其他所有物種”的境地。在 AI 與其他所有物種共存的未來,在他看來,人類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成為 AI。
Elon 將人類大腦數字三生細胞壁(tertiary layer)比喻為巫師帽。概念是指全腦界面將變為如同將設備植入大腦,使大腦變為設備。
二、AI 系統將和大腦融合無間
你的設備賦予你半機器人的超級能力,并作為通往數字世界的窗口。巫師帽的電極陣列是一種新的大腦結構,與大腦邊緣系統及大腦皮質并列。(對于大腦邊緣系統、大腦皮質等基本結構的介紹,請見后文。)
但大腦邊緣系統、大腦皮層質及巫師帽僅僅是硬件系統。當邊緣系統在工作時,與你交互的并不是該物理系統,而是其間的信息流。這是一種物理系統內部的活動反映在意識中,使你感受到憤怒、恐懼、饑渴或饑餓。
大腦皮質是同樣道理。包裹著你大腦的物質存儲并管理信息,但是當你思考、觀察、聆聽或感受的時候,你體驗到的是信息本身。視覺皮層本身對你來說沒有任何作用,是其間的光子信息流給你帶來一個視覺皮質的體驗。當你挖掘你的記憶時,你不是在尋找神經元,而是在搜索存儲在神經元的信息。
大腦邊緣系統和皮質只是大腦灰質。是灰質間的活動流形成了你熟悉的內在特性,動物本能的大腦和人類理性的大腦。那么這對數字三生細胞壁又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盡管大腦中存在的是物理設備,但是電極陣列本身,即你將體驗及了解的三生細胞壁的組成部分,正是陣列間流動的信息。
正如邊緣系統產生的感受及欲望以及大腦皮質產生的思想和低語在你感受來都如同你的一部分,你的內在,在巫師帽中發生的一切活動也將帶來同樣的感受。
Elon 對于 Wizard Era 的展望只是巫師帽應用之一,其中一個核心的目的為將其作為大腦及基于云端的定制AI系統之間的交互界面。他相信這一 AI 系統將以和你的動物本能大腦和人類理性大腦同樣的特性存在。
他這樣講:可以想象,是可能有種方式使得三生細胞壁令人感受到它是人的一部分。它不是卸載的對象,它就是你。
寫下來看著挺有道理。你用大腦皮質完成大多數思考,但是當你餓了,你不會說“我的邊緣系統餓了”,而是“我餓了”。同理,Elon 認為,當你解決問題時,AI給出解決方案,你不會說:“我的 AI 想到了!”,而會說:“我想到了!”當你的邊緣系統想偷懶,而你的大腦皮質想工作時(我經常有此經歷),你感覺并不是在跟某些外部力量斗爭,而是你自己想嚴格要求自己。同理,當你采取了某些策略,而你的 A I反對時,真實的意見相左和爭論就會發生了,但這感受起來也是一種自我的內心斗爭,而不是在與你思考中產生的另一方在爭論。這種爭論感覺上和思考一樣。
總之寫下來看著確實挺有道理的。
但我最初聽到 Elon 談論這一概念時,總覺得不大對。不論怎么努力嘗試理解,我總是忍不住用我比較熟悉的概念去套用,例如這就類似我腦中可以聽到它說話,或者甚至可以一起思考的一個 AI 系統。在這些場景中,這個 AI 看上去還是一個與我交流的外部系統,并不像我。
之后有一天晚上,當我在重讀 Elon 之前的一些論述時,我頓悟了。AI 可以成為我,完完全全地。我明白了。
但之后我又搞不明白了。第二天當我試圖向另外一個朋友解釋我的頓悟時,我把我倆都搞暈了。我又回到持有“等等,這個 AI 不可能真的成為我,它還將是在和我交流“這種想法的境地。自那之后,我的想法反反復復,無一善終。這種狀態就類似有那么一個瞬間,時間變成相對的,時空只是單一一層。似乎有那么一瞬有種直覺,時間變慢而你變得很快。然后我又迷失了。我在寫下上述幾句的時候,直覺又不存在了。
成為 AI 最難的一點在于它結合了兩個無意識的概念:大腦界面和大腦界面可以賦予你的能力與通用人工智能。今天的人類還不具備理解其中任一項的知識。無論我們自認為想象力多豐富,我們的想象力僅僅是基于我們的生存經驗,而上述概念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這就如同嘗試去想象一種從沒見過的顏色。
這就是為什么當 Elon 談論他的信念時,我在信服和盲從之間徘徊。不過考慮到他在七歲時就已經理解時空觀,且懂得如何殖民火星,我傾向于多聽聽他怎么說。
帶寬是腦機融合的關鍵
他談到的是這一切都跟帶寬有關。很顯然,如果想讓巫師帽能發揮作用,帶寬意義重大。但 Elon 認為,如果要成為 AI 而不是使用 AI,與 AI 連接時,帶寬不是可供選擇的,而是必備的。
他是這樣考慮的:通信帶寬速度非常慢,尤其在輸出時,這是挑戰所在。當你使用手機輸出信息時,你兩根拇指移動的速度非常之慢。如果帶寬過低,與 AI 的互動程度就會非常之弱。基于低帶寬的限制,這種互動基本是無意義的。AI 基本就會我行我素,因為速度太慢沒有溝通可言。溝通速度越快,融合程度越高,溝通速度越慢,融合程度越低。我們與 AI 分離程度越高,AI越偏離我們,最終倒戈相擊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AI與我們越來越疏離,智能水平又遠高于我們,如何能確保他們不生成與人類利益背道而馳的優化機制?但是如果我們能實現一種緊密的共生關系,AI 就不是“非我”,而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并將與我們形成類似皮質與大腦皮質和邊緣系統之間關系近似的關系。
Elon 視通信帶寬為決定人機融合程度的關鍵因素,同時將人機融合程度視為我們未來在AI世界中生存的關鍵因素:我們或者被遠遠拋在身后,全無用處,被當做寵物(如家貓)對待;或者最終找到某種與AI共生及融合的方式。之后他補充道:能被當做家貓還是算是不錯的結局呢。
在完全無法想象未來充斥著 AI 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前提下,在超級智能時代到來之前,通過人機融合實現對人類物種的保護聽起來挺靠譜。AI 時代人類可能會受到的威脅將來自于利用 AI 作惡的人類以及與人類利益相悖的 AI。當絕大多數人類都能控制一部分 AI,與 AI 共同思考,利用 AI 自我防御,或通過與 AI 融合,進而基本上能完全理解 AI 的想法,人類就處于不那么危險的境地了。
人類會變得從未有過的強大,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但是如 Elon 所講,如果人人都是超人,單個人就很難造成大面積傷害,會有很多限制和平衡加以制約。人類也因此不太可能對 AI 整體完全失控,因為 AI 將以多種目的廣泛存在。
但時間是關鍵,Elon 強調,向這一方向努力的進度至關重要。數字超級智能的發展程度不應該超過腦機融合界面實現程度太多。
我在考慮上述問題時,顧慮在于人類的全腦界面是否足以支撐這種人機融合的實現。我向Elon提出了這一顧慮,并指出人腦思考的速度和計算機的處理速度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他答道:是的,但是根據數量級順序增加帶寬會改善這一情況。方向也是正確的。能解決所有問題嗎?不能。但是方向對嗎?是對的。如果一定要向一個方向走,為什么不選擇這一個?
這就是 Elon 設立 Neuralink 的初衷。
Neuralink 團隊:從1000人中篩選9人
在寫作過程中,我有機會采訪到 Neuralink 創始團隊一半的成員,下面給大家介紹一下 Neuralink 的創始團隊。
Paul Merolla,過去七年里擔任 IBM 首席芯片設計師,負責 SyNAPSE 項目,領頭開發了 TrueNorth 芯片。Paul 說他專注的領域被稱為神經形態學(neuromorphic),其目標是根據大腦結構的原理設計晶體管電路。
Vanessa Tolosa,Neuralink 的微織造(microfabrication)專家,也是生物相容性材料(biocompatible materials)領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Vanessa 的工作設計根據集成電路的原理設計生物相容性材料。
Max Hodak,在杜克大學 Miguel Nicolelis 的實驗室開發開創性的 BMI 技術,同時每周兩次在大學和 Transcriptic 公司之間往返,Transcriptic 是他創立的“生命科學機器人云實驗室”。
DJ Seo,二十多歲時在 UC Berkeley 設計了一種尖端的新型 BMI 概念,叫做“神經塵埃”(neural dust),是一種微型超聲波傳感器,為記錄大腦的活動提供了新的方法。
Ben Rapoport,Neuralink 的外科專家,也是一名頂級的神經外科醫生。他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電氣工程博士學位。
Tim Hanson,他曾是“地球上最好的全能工程師之一”,他自學了材料科學和微織造方法,開發了 Neuralink 將會使用的一些核心技術。
Flip Sabes,是 USCF 實驗室的主管研究員,他結合“皮質生理學(cortical physiology),計算與理論建模,以及人類心理物理學和生理學”,開創了 BMI 的新領域。
Tim Gardner,它此前是 BU 的主管研究員,他的實驗室對鳥類植入 BMI 進行研究,以了解“基本神經單元如何組合創造復雜的歌曲”,以及“不同時間尺度神經活動模式之間的聯系”。
然后就是 Elon Musk,他既是 Neuralink 的 CEO,也是團隊的一員。在談到神經科學時,馬斯克顯然是團隊中專業知識最少的一員。但他也創立了 SpaceX,他同樣也沒有多少航天知識,但是通過閱讀和咨詢專家團隊迅速成為一名受到認可的航天科學專家。在 Neuralink,這很可能再次發生,因為,他說:“沒有深刻的技術理解,我認為很難做出正確的決策”。
我問馬斯克,它是如何找到這個團隊的。他說,他起碼見了超過 1000 人,最后形成了這樣一支團隊。最大的挑戰是公司需求的完全獨立的專業領域太多,例如神經科學,腦外科,微電子技術,臨床試驗等等。他想找到跨專業的專家。你可以看到,這支團隊里每個人都將自己獨特的交叉領域帶到一起,組成一個共同的大的專業領域(mega-expert)。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組合。
?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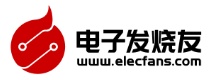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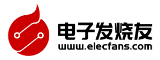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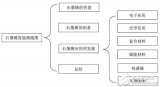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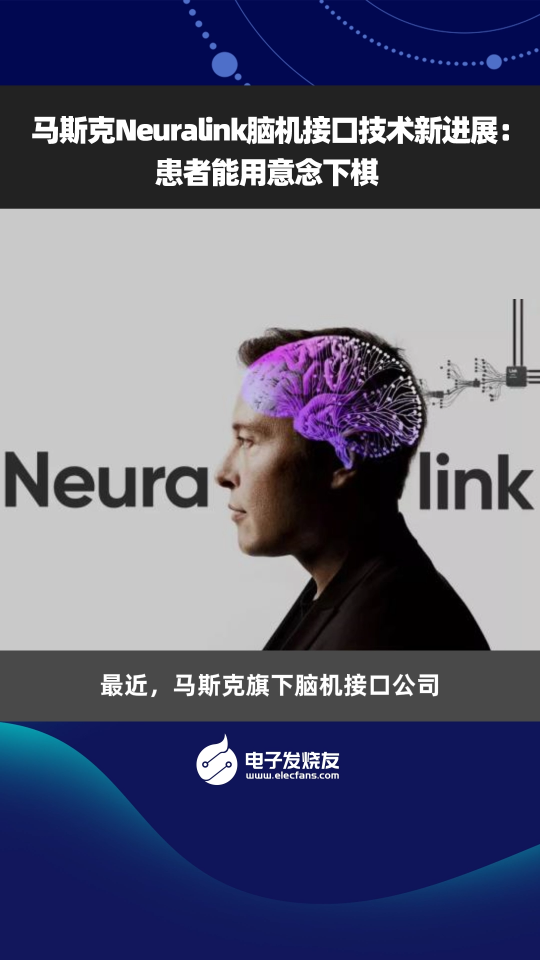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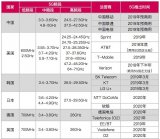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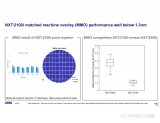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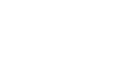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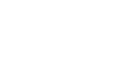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