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美國啟動過一個 “人類腦計劃”(Human Brain Project US),目標是建立一個全球網絡,分享有關腦科學的所有數據,當時多國(包括我國)響應,科學工作者歡欣鼓舞。后來,此項目無疾而終,再也沒有人提及此事了。
尷尬的 “訃告”
7 月底,國內許多科普公眾號突然發布頭條新聞,以鋪天蓋地之勢報道了歐盟人腦計劃失敗的新聞,所用的標題也非常吸引眼球,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勢。
但是,如果稍仔細讀一下,就會發現所有這些文章都源自 Ed Yong 今年 7 月 22 日發布的一篇推文《人腦計劃并未實現其諾言》(The Human Brain Project Hasn’t Lived Up toIts Promise),講的是在瑞士工作的以色列科學家馬克拉姆(Henry Markram)(圖 1)2009 年 7 月 22 日在 TED 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宣稱他可以在十年內做到在計算機上仿真人的全腦(那時他還沒申請人腦計劃呢),到今年 7 月 22 日正好是十年,而他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圖 1. HBP 的發起人馬克拉姆和他心愛的鼠皮層柱微回路仿真結果。(引自 http://img.clubic.com/02BB000007384273-photo-henry-markram.jpg)
實際上,正式啟動于 2013 年的歐盟人腦計劃(Human Brain Project,下文簡稱 HBP)早已在 2015 年就公開放棄了這一目標,馬克拉姆也從人腦計劃說一不二的領導崗位上黯然下臺[1]。
所以 Yong 的標題并不錯,雖然有些 “馬后炮” 了。如果說馬克拉姆的人工全腦之夢已死,那么這個訃告發得晚了些。而如果說整個歐盟人腦計劃(HBP)已經死了,這個訃告發得又有些早了。該計劃要到 2023 年才到期,官方網站(https://www.humanbrainproject.eu/)到現在也還在運轉,并不斷發布新聞,7 月 26-28 日 HBP 的負責人 Alois Knoll 博士還到上海參加 “2019 類腦智能研討會” 呢。
現在的人腦計劃和馬克拉姆當年提出時的人腦計劃的目標已大相徑庭。現在的人腦計劃已經力圖變成一個基于信息學通訊技術的研究腦、認知神經科學和仿腦計算的公共平臺,變成有某種永久性共享基礎設施的國際組織[2]—— 雖然到 2023 年,這一縮小了的目標是否能成功,甚至 2020 年進入最后階段時歐盟是否還會繼續撥款,都還有待觀察。HBP 最終是否能成功,將取決于廣大神經科學家是否愿意利用這個平臺來進行研究,并且得出有意義的結果。不過,不管這個計劃現在究竟是白白胖胖還是骨瘦如柴,但至少還沒有壽終正寢。 至于有些報道中說歐盟人腦計劃(EUHuman Brain Project, HBP)是藍腦計劃(BlueBrain Project, BBP)的改稱,則是不對的。藍腦計劃是馬克拉姆 2005 年在瑞士聯邦政府支持下在他所在的瑞士聯邦洛桑理工學院啟動的一個計劃,一直運行至今。馬克拉姆確實是在藍腦計劃的基礎之上,聯合了其他科學家提出人腦計劃的,但這依然是兩個不同的計劃,藍腦計劃也有自己獨立的官方網站(http://bluebrain.epfl.ch/),馬克拉姆現在的工作多以此計劃的名義發表[3]。 以上僅僅是厘清一些基本的事實。本文的目標主要是想檢討一下馬克拉姆提出 “用大科學計劃的形式實現人工全腦” 失敗的原因是什么,給我們帶來了哪些經驗教訓。 致命缺陷
關于馬克拉姆 “仿真全腦計劃” 的失敗,Yong 在文章里列舉了不少原因,歸結起來大概有下面這幾點:
①我們對腦的認識還很膚淺,未知之處多于已有的認識; ②其目標不是針對某個特定問題,而是為仿真腦而仿真; ③犯了循環邏輯的錯誤,即用仿真腦的方法來認識腦,而為了仿真腦又必須先認識腦。 以上確實是問題所在,不過在筆者看來,Yong 還沒有深入談到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其實,不用等到今天,只需回顧一下藍腦計劃的過去,以及以往大科學計劃的成敗,就不難預見到馬克拉姆的失敗。 2013 年 HBP 剛開始啟動時,筆者就發表過一篇題為《歐盟人腦計劃不大可能在十年內創建一個人工全腦》(The Human Brain Project EU Is Unlikely toCreate an Artificial Whole-Brain in a Decade)的評論文章[4]。2014 年,筆者又在拙作《腦海探險:人類怎樣認識自己》[5]一書中對 “十年內造不出人工全腦” 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在這里,我們先提一個仿真全腦計劃最主要的致命傷:腦科學還沒有任何理論框架。 回顧歷史,所有成功的大科學計劃實質上都是一些工程技術性的計劃,如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探月的阿波羅計劃,以至分析 DNA 序列的人類基因組計劃,這些計劃的后面都有堅實的理論基礎。而美國尼克松總統提出的 “向癌開戰法案” 就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 —— 它雖然意義重大,卻無疾而終。仿真全腦計劃也存在這一缺陷:人的全腦是怎樣工作的,我們至今甚至還沒有任何理論框架。
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前,1968 年,為了紀念控制論誕生 20 周年,科學家曾經開過一次討論會,當時一些科學家就曾經斷言,神經科學的情況就像 19 世紀末元素周期表發現之前化學的情況: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實驗資料,但是缺乏一個理論框架把這些資料組織起來。差不多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理論框架依然沒有出現。
腦科學的現狀讓我想起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分子生物學和胚胎學的狀況。發現了許多有趣的事實,每年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穩步的進展,但主要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而要是沒有新的技術和新的思路,那么這些問題也不大可能得到解決。分子生物學在 20 世紀 60 年代變得成熟了,而胚胎學才剛剛開始成熟。腦科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個學科的魅力和答案的重要性將不可避免地將其推向前進。[6]
——DNA 雙螺旋結構發現者克拉克,1990
今天的神經科學還處在法拉第階段,還沒有到麥克斯韋階段,要想一步登天是毫無意義的。[7]
—— 印度裔美國神經病學家拉馬錢德蘭,1998
2006 年,當我為將要創刊的《認知神經動力學》(Cognitive Neurodynamics)雜志起草發刊詞時,曾請美國神經科學家弗里曼(Walter J. Freeman)審閱,他在我的草稿里加了一段: 五十多年前,受到發明數字計算機和建立遺傳的 DNA 模型的鼓舞,科學家們滿懷信心地認為,認識生物智能和創造機器智能的任務已經勝算在握。在開始時,進展看上去非常迅速。占滿空調房間的巨大電 “腦” 縮小到可以放到手提包里。計算速度每兩年就翻一番。 這些進步所顯示出來的其實并非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困難性。我們就像那些 “發現” 了美洲的地理學家一樣,他們在海岸上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串小島,而是有待探險的整個大陸。使我們深為震驚的與其說是在腦如何思考的問題上我們作出的發現的深度,還不如說是我們所承擔的闡明和復制腦高級功能的任務是何等的艱巨。[8] 這是我寫不出來的,因此就全文照錄。我以為,弗里曼的這段話到現在也依然成立。缺乏全腦工作機制的理論框架,在腦研究中依然有大片幾乎空白的領域有待勘探,這些現狀是馬克拉姆無法兌現承諾的致命傷。 清醒的認識
人腦計劃被提出而尚未正式啟動之時,在科學界就已經引起了極大的興趣,許多人非常興奮,但是也不乏像筆者這樣的懷疑論者。當我和某位同事討論時,這位同事好心地勸告我說:“這些都是些聰明人,他們不會想不到連我們也能想到的問題。” 這話并非沒有道理。其實馬克拉姆本人對此并不糊涂,2009 年,在尚未更新過的藍腦計劃官網上,他回答了一些提問,表現出清醒的認識。關于進一步建立全腦模型(開始是鼠腦,最終是人腦)的問題,馬克拉姆是這樣說的: “以目前和可預見未來的計算機技術而論,看來還不大可能仿真一個精確到細胞和突觸復雜性水平(分子層次以上)的哺乳動物腦。”
問:你是否相信計算機真的能確切地仿真人腦?
馬:以目前和可預見未來的計算機技術而論,看來還不大可能仿真一個精確到細胞和突觸復雜性水平(分子層次以上)的哺乳動物腦。…… 這很少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要這樣做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腦內的每個分子就是一臺功能強大的計算機,而我們得仿真以千兆(trillion)計的分子的結構和功能,還得仿真這些分子相互作用所遵循的全部規律。你至少需要比現在大 1012(trillion)倍和快 1012倍的超級計算機。哺乳動物自己就能繁殖,我們無需用計算機來復制哺乳動物。這不是我的目的。我們只是想認識生物系統是如何工作的,又為什么會失常,這將造福人類。”
問:我們真的能造出一個這樣的人工大腦,它會有意識嗎?
馬: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意識僅僅是由非常大量的相互作用產生的,那么也許有可能吧。但是我們對意識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很難說。 當然,這些問答在現在的 HBP 網站或藍腦計劃網站上已經找不到了。這些全是筆者當年下載下來保存在電腦里的資料。 急轉直下
馬克拉姆當時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和筆者之前對人腦計劃的估計基本是一致的。轉折點出現 2009 年。正如 Yong 所說,馬克拉姆在 2009 年 7 月 22 日 TED 組織的大會上一反不久前的清醒認識,宣布要在十年內造出人工全腦。緊接著,在同年 12 月出版的《發現》(Discover)雜志對他的專訪[9]中,他表示:“我想我能夠有充分把握地說,建立起一個腦模型是完全可能的。” 當記者問 “什么時候您才能仿真人腦,而不只是某個部分的鼠腦” 時,他的回答是: “這只是一個尺度的問題,也是一個精度的問題…… 從技術層面上講,利用計算機和數據采集技術,有可能在 10 年內建立起人腦模型。實際上唯一的問題是經費問題。不過這得一步步來。下一步我們要花 3 年時間建立大鼠的全腦模型,以及分子層次上鼠腦中 2 億個神經元相互作用的精細模型。” 對于記者進一步的問題 “一旦我們建立起人腦模型,我們是否就能體驗并重建人的心智?” 他的回答是:
這并非真的那么復雜。為了使我能讀出你的思想,我需要能看到你的模式,并把它轉換成讀出…… 這就是神經編碼。
由于我們正變得更善于對神經信息進行解碼,我想這將不會成為多大的問題。…… 我們已非常接近于解決神經編碼問題,所有一切都表明在未來的幾年里就會有很大進展。
為什么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在科學上沒有出現任何突破的情況下,會產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筆者以 “小人之心” 猜度,恐怕其原因就出在他的那句話 “實際上唯一的問題是經費問題。”不過這并不是筆者的憑空猜測,種種蛛絲馬跡都暗示著這個原因。
首先是時機。在馬克拉姆開始其藍腦計劃的時候,IBM 以極其優惠的價格供應了一臺當時最先進的藍色基因(Blue Gene)超級計算機,大概是由于 IBM 的外號叫做 “大藍”(Big blue)的原因吧,馬克拉姆把他的計劃也叫做了藍腦計劃。無疑,他希望 IBM 能長期給予資助。但是后來,他發現在 IBM 內部有一個以莫德哈(Dharmendra Modha)為首的競爭者,他們用點神經元仿真了一個貓腦規模的神經網絡,而當 IBM 顯示出更偏向自己人的時候,馬克拉姆很可能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以致在 2009 年給 IBM 的 CTO 邁耶森(Bernard Meyerson)寫了一封異乎尋常的信件,并且抄送了許多媒體。在這封信里,他對莫德哈大加攻擊,用 “騙局”、“彌天大謊”、“愚蠢” 等等詞匯來形容莫德哈的工作,甚至說出 “我曾以為會有一個倫理委員會把這個人倒吊起來” 這樣一般在正常的學術爭論中不會使用的重話[10]。這使人不得不懷疑,馬克拉姆和自己期望的贊助商 IBM 關系搞崩了。 而正在這個時候,即 2009 年 12 月,歐盟宣布要資助兩個 2013-2023 年度高風險、但可能帶來巨大變革的 “未來和新興技術(futur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FET)旗艦項目(flagship projects)”,每個項目的資助額為 10 億歐元,為期 10 年。馬克拉姆作為 27 名顧問團的成員之一,自然在第一時間就知道了這一消息。
“近水樓臺先得月”,馬克拉姆搶得先手,以藍腦計劃為基礎,在經過近兩年的籌備之后,聯合了歐洲 19 個國家的 117 個研究單位,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以 “人腦計劃” 為名贏得了歐盟公開招標的 “未來和新興技術旗艦項目”,并在同年 10 月 7 日正式啟動。 為了贏得這樣一個高風險而又可能帶來高回報的旗艦項目招標,還有什么課題能比 “在計算機里仿真出一個人腦” 更讓人印象深刻呢?再說,以這樣一位卓有貢獻的著名神經科學家領銜,聯合了那么多科學家共同提出的項目,怎么可能是一場騙局呢?
圖 2. 人腦計劃要把從離子通道到全腦的所有知識都整合在一個模型之中。圖中從上到下顯示的是腦的各個層次:生物大分子層次、細胞層次、回路層次、區域層次和全腦層次。馬克拉姆已經在超級計算機 “藍色基因” 上仿真了最前面的三個層次,現在他想進一步仿真最后兩個層次。[11]
更何況,馬克拉姆在執行藍腦計劃時,也確實在腦的最底層的三個層次(圖 2,頂上的 3 個層次)作出了成績。他們在 2005 年建立起三維的生物學真實性的神經元模型,在這些神經元模型中考慮了 200 種不同的離子通道及其在細胞膜上的分布,還有神經元的形態。2009 年他們在一臺超級計算機上構建了一個出生 2 周后大鼠的新皮層柱模型,其中包括 10,000 個簡化的神經元模型;同時考慮了幾百種不同類型神經元在新皮層柱中的分布與密度,每個神經元又可能跟好幾千個神經元發生聯系…… 這無疑令人相信,人腦計劃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至于一些使人感到懷疑的地方,則往往被擱置一邊。畢竟,“這些都是聰明人,怎么會想不到你我所能想到的問題呢?” 論點與漏洞
為了給人腦計劃立項大造聲勢,馬克拉姆在 2012 年 6 月的《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人腦計劃》(Thehuman brain project)的文章[11],全面闡述了他的思想。
他曾在突觸可塑性等方面做出過很出色的工作,但是在文章中,他聲稱:
我知道我在我的科學生涯上可以再這樣二、三十年地做下去,但這無助于我認識腦是如何工作的。
(神經科學領域)每年都會發表 60,000 篇有關腦研究的論文,每篇都是出色的研究,但是每一篇都局限于一隅。
馬克拉姆認為,如果按照常規辦法,在各種條件下對各物種的各個年齡段,并在健康的和各種疾病的條件下,逐個測量腦里面的每個基因、蛋白質、細胞、突觸與回路,那么即使再過一個世紀或者更長時期,也還是解決不了問題。為克服這一困難,必須把全世界所有已知的和新研究出來的數據都整合在一起。這樣就必須研發全新的信息和計算技術 —— 包括超級計算機 —— 借以把這些數據整合在統一的計算機模型之中,并對腦進行仿真。 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發現腦的工作模式和組織原理,找出我們人類知識的缺失之處,并以新的實驗來填補空缺。他相信,在這樣做了以后,就可以從已知的知識預測其他未知之處。他認為,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將闡明神經回路是如何組織起來的,行為和認知是怎樣產生的(圖 2)。 這就像剛到新大陸的探險家,覺得要深入內陸,一塊一塊地勘探太費時間,就提議 “讓我們根據現有知識來造一個沙盤模型吧,只要有了這個模型,我們就能把所有的知識組織起來,我們的勘探也就可以完成了”。當然勘探新大陸并沒有多少層次的問題,比起研究腦機制來說要遠遠簡單得多。即便如此,我想探險隊中的其他成員恐怕也不會有多少人同意的。 馬克拉姆在《人腦計劃》一文中說道: 我們的研究方法的關鍵在于精心研究腦賴以產生的基本藍圖:也就是在整個進化過程中、并在胚胎發育過程中再一次構造出腦的整套原則。從理論上來說,這些原則正是我們動手建造腦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人們的質疑不無道理:這些原則所生成的復雜性是驚人的 —— 所以我們才需要超級計算機來解決這個問題。不過發現這些原則本身要好辦得多。如果我們找到了這些原則,那么從邏輯上來說,我們沒有理由不能利用生物學上產生腦的藍圖去同樣建造一個 “硅腦”。
在筆者看來,不幸的是,正如馬克拉姆向媒體發表的許多宣傳那樣,這段話也用了 “如果我們找到了這些原則” 的假設語氣 —— 要知道,“這些原則” 可以說正是整個神經科學研究的對象,“如果” 我們發現了所有這些原則,那幾乎將是神經科學的終結,而這在可預見的未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上述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馬克拉姆似乎認為建立腦研究的理論框架 “好辦得多”,而其實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腦是我們已知宇宙中最為復雜的系統,它有著極多的層次(圖 2 中其實只畫出了最粗劃分的層次),在每個層次上都會產生下一層次所沒有的 “涌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y)。對腦的認識,我們還有大量的未知領域,而不只是馬克拉姆所講的 “縫隙”(gap)而已。 例如馬克拉姆自己承認的、對腦功能十分重要的膠質細胞,我們現在就還很不了解。盡管已研究了好幾十年,但是至今仍所知不多。假如仿真人腦計劃推進到需要在模型中納入膠質細胞的時候了,誰能保證神經科學家就一定能按馬克拉姆的要求搞清楚了膠質細胞的功能和機制? 突破性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工程計劃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前者很難按計劃安排,靈感和運氣常常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單靠汗水未必能按部就班地揭開某個自然之謎。馬克拉姆自己也說過,為了揭開人腦之謎需要幾十位愛因斯坦,但是愛因斯坦可沒法用計劃生產出來。 此外,為了彌補某個缺失的知識,建模者將不得不引入假設。但是腦科學中的未知領域是如此之多,如果都要用假設來填補,那么假設就會多得不可能來檢驗這些假設的真偽。 關于馬克拉姆設想中的其他漏洞,筆者在以前的著述中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3-5],在這里不再重復。
雖然馬克拉姆在藍腦計劃中取得的成就給人以 “人腦計劃實際可行” 的錯覺,但實際上,對于一個有極多層次的系統來說,越是上層的問題,解決起來就越困難。正如要想研究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所用顏料的化學成分是相對容易的,但即使你完全搞清楚了這些成分的性質和分布,你依然難以解釋 “蒙娜麗莎為什么美”。 實際上,馬克拉姆以后的工作一直停留在腦的前三個層次上(生物大分子層次、細胞層次、回路層次)。2009 年,馬克拉姆在接受《發現》雜志采訪時,曾承諾在 3 年內 “建立大鼠的全腦模型”,到 2013 年他啟動人腦計劃時,3 年早已過去,但他又把之前的承諾列入計劃,這表明當初的許諾并未兌現。2015 年,他發表了鼠皮層柱中非常小的一塊的仿真結果,并聲稱他已兌現了他的承諾 —— 他似乎忘記了,或是假裝忘記了 “三年內仿真大鼠全腦” 這回事。他的承諾就像是吊在驢頭前面的胡蘿卜那樣,永遠可望而不可即,實在使人懷疑。 亡羊補牢
可以說,馬克拉姆許下的 “在 2023 年建立人工全腦” 的諾言實際上早在 2015 年就已宣告死亡。但是,歐盟人腦計劃徹底改組了領導班子,重新擬定了目標 —— 建立基于信息學通訊技術的研究腦、認知神經科學和仿腦計算的,有某種永久性共享基礎設施的國際組織 —— 倒是一直運轉至今。雖然 HBP 已徹底放棄了馬克拉姆所提的目標,但依然取得了某些成就。
1. 初步建成信息平臺
2016 年 3 月底,HBP 的起飛階段到期。歐盟組織了十幾位專家對起飛階段的工作進行評估。評審專家認為,歐盟人腦計劃已經克服了初期困難,初步建立了神經信息學、腦仿真、高性能計算、仿神經結構工程、神經機器人和醫學信息學等六個信息學通訊技術平臺。HBP 還建立了一個協作實驗室(Collaboratoy),在該實驗室的網上入口登錄后,就可以進入所有平臺,讓研究者使用其軟件和數據庫,初步具備了向計劃內外研究者開放的條件。 HBP 號召全世界神經科學界都來使用這些平臺。但是目前該計劃外的研究者對此號召作何反應還不清楚。德國計算神經科學家赫茲(AndreasHerz)評論說:“眼下還沒有人能說這些研究平臺是否成功。”[12]對于改革后的 HBP 來說,這些平臺是否能得到計劃內外的神經科學家的廣泛應用,他們又能否在此平臺上得出有意義的成果,將是判定改革后的計劃是否成功的主要標志。
2. 建立一個有生物學真實性的鼠微皮層回路模型
HBP 在神經科學和仿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項標志性成就,那就是建立了一個有生物真實性的微皮層回路模型[12]。這一工作歷時 20 年,由國際上 82 位科學家合作,仿真了幼鼠體感皮層中一塊 1/3 mm3大小的組織,相當于一個功能柱。其中包含 3 萬個神經元和 4000 萬個突觸(圖 3)。
圖 3. 數字重建鼠體感皮層微型回路。自上至下各行:(頂圖)采集實驗數據。(中圖)從解剖結構和生理電性質上重建硅神經細胞。(下圖)左:當令鈣離子濃度從低到高增大時,仿真結果得出網絡在兩種定性上不同的動力學狀態之間翻轉;右:由仿真結果預測的生物實驗結果。[13] 研究人員分析了這些神經元的形態、在皮層各層中的分布和放電模式,據此區分出 207 種不同的神經元類型。再按照不同類型神經元在此柱狀組織中的密度,在仿真組織中安排虛擬神經元的分布。每個神經元的細胞膜都像霍奇金 - 赫胥黎模型那樣考慮了 13 種不同的離子通道(均與跨膜電位以及鈣離子濃度相關),最終在這些虛擬神經元之間建立起 3700 百萬個突觸聯接。不過,由于缺乏實驗資料,對突觸聯接可能存在的不同類型不得不進行假設。 這樣仿真得到的結果和動物實驗吻合得很好。例如,兩者的行為都和細胞外鈣離子濃度以及細胞體的去極化程度有關:細胞外鈣離子濃度控制網絡對突觸輸入的響應模式,而去極化程度則控制神經元的自發發放。控制這兩個參數就可以讓網絡在兩種不同性質的動力學狀態之間翻轉(圖 3)。 美國神經科學家科赫(Christof Koch)稱此工作為 “迄今為止對一塊可興奮腦物質所進行的最完整的仿真。考慮到在該模型中做了極大數量的近似和外推,這些神經元既沒有像癲癇放電那樣亂放一氣,也不像昏迷那樣沉寂,而在一級近似之下就像腦片上的神經元那樣活動,這本身就是一種卓越的成就。”[14] 不過這一 “標志性成就” 并未得到科學界的一致稱贊。一些科學家認為這一長達 36 頁的工作正好說明了重建全腦的思想是一種誤導和浪費金錢。德國神經科學家黑爾姆施泰特(Moritz Helmstaedter)認為有工作發表當然好,不過卻證實了他最壞的擔憂。他說,這一計劃 “被極度夸大了,而現在所發生的正是我們所擔心的:并沒有真正的發現。把大堆數據堆砌在一起并不能創造出新科學。” 英國科學家萊瑟姆(Peter Latham)說:“我認為人腦計劃純屬浪費金錢,不過在讀了這篇文章之后,我的觀點略有變化,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救了人腦計劃。” 不過,萊瑟姆接著問道:“您可愿意花 10 億歐元來做這些事?這才是問題之所在。”[15]
3.仿神經結構芯片
在歐盟人腦計劃仿神經結構計算平臺(NeuromorphicComputing Platform)下有兩個項目:一個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弗伯(Steve Furber)領銜的 “脈沖發放神經網絡構筑”(Spiking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SpiNNaker)項目,另一個是由德國海德堡大學的邁爾(Karlheinz Meier)領銜的 “仿神經結構混合系統腦啟發多尺度計算”(Brain-inspired multiscale computation in neuromorphic hybrid systems,BrainScaleS)項目,二者都在硬件上實現了仿神經結構芯片(neuromorphic chip)。這些系統中的人工神經元數量都達到了百萬級或以上,而消耗的能量要比在傳統計算機上仿真有同樣節點數的神經網絡降低 4 個數量級以上。 這些系統的共同特點是采用脈沖發放神經元作為基本元件,并用脈沖進行通訊,大大提高了速度、減少了能耗。這些芯片在一些特別需要節能的場合也許會有應用前景,但是能否成為新一代計算機,則取決于它們在其他性能上是否顯著優于傳統計算機,以及使用者是否愿意放棄早已駕輕就熟的傳統計算機技術。另外,這些芯片能否實現有應用前景的功能,能否從頭建立起自己的語言和生態系統,都還不得而知。 從筆者已看到的材料來看,這兩個系統似乎還不如它們的競爭對手 —— 馬克拉姆揚言要 “倒吊起來” 的莫德哈所開發的神經結構系統 —— 真北系統(TrueNorth Systems)。后者至少已能做到實時識別環境中的不同對象,如行人、騎車人、卡車、汽車、大巴等,并且比傳統系統的速度要快得多,能耗少得多。另外,真北系統還開發出了軟硬件環境,也就是所謂的 “生態系統”(ecosystem),現在已經可以運行深度學習和卷積網絡。為了推廣真北系統,IBM 甚至成立了一所虛擬的網上大學來進行新語言的編程教學[16]。盡管如此,仍很難說工程技術人員是否愿意使用新系統,因此這類系統的應用前景尚有待觀察。但不管怎么說,筆者認為作為一種試探,研究開發仿神經結構系統是必要的。 此外,SpiNNaker 和 BrainScaleS 兩個項目都強調了其主要目的是用硬件模仿腦。SpiNNaker 系統于 2018 年末建成,研究人員希望能用這個系統模擬鼠腦中的一億個神經元,而目前在做的也只不過是模擬微功能柱。由于我們對神經回路及其以上層次的聯結都還不清楚,這樣做究竟只是建立鼠腦規模的人工系統,還是真正模擬鼠腦,還有待觀察。或許這種希望和當年馬克拉姆的允諾類似 —— 只不過前者用了仿神經結構系統,速度更快,能耗更低,而后者則是在傳統計算機上用軟件來做的。
圖 4. SpiNNaker 系統。(左上圖)SpiNNaker 芯片;(右上圖)由 48 個芯片構成的電路板:(下圖)由電路板構成的 SpiNNaker 系統。(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by Steve Furber and colleagues) 展望
2016 年 4 月,HBP 終于進入正式實施階段。在經過了起飛階段的激辯、重組以及外部同行評審之后,HBP 在目標中去掉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承諾,主要是放棄了馬克拉姆當初 “十年建立人工全腦” 的許諾。在堅持對腦進行多層次和多學科研究,并強調使用建模和仿真方法的同時,更強調要開發用于腦研究的多種信息學通訊技術平臺,并建成永久性的歐洲腦科學研究設施。
2016 年 11 月 12 日出版的《神經元》(Neuron)雜志
《神經元》(Neuron)雜志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出版了有關各國腦計劃的一期專刊,HBP 的新領導集體發文宣布其目標如下[2]:
HBP 是一個為期十年的歐盟旗艦計劃,其目標是在多個尺度上重建腦組織。這一計劃在所有層次上把實驗、臨床數據、數據分析和仿真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就能最終在各個層次之間架設起橋梁。HBP 的信息學和計算機構筑是獨一無二的,它利用云技術進行合作,研發出具有數據庫、工作流程系統(workflow systems)、千萬億字節(petabyte)存儲和超級計算機的各種平臺。人腦計劃將發展成推進腦研究、醫學和仿腦(brain-inspired)信息技術的歐洲研究設施。 HBP 提出了一種獨特的基于信息技術的策略,這一策略把全世界的神經科學數據整合在一起,多層次地認識人腦及其疾病。因此目前所有的這些平臺原型將逐漸轉變為更為可靠的、對用戶友好并緊密地整合起來的研究基礎設施。成立一個 HBP 法人實體,將為不受計劃時間限制的、永久性的基礎設施奠定組織基礎。 這一目標雖然遠不及原計劃那樣野心勃勃,不過還是相當宏大。到 2023 年期滿時,這個縮小了的目標能否實現,將取決于這些平臺是否實用,廣大神經科學界是否愿意使用這些平臺,并在其上做出有突破性意義的成果。除了該計劃內部的成員單位及合作單位之外,神經科學家和醫生是否愿意與其共享數據都是大問題。
1993 年,美國神經科學家科斯洛夫(S.H. Koslow)也曾啟動過一個美國版的 “人類腦計劃(HumanBrain Project US)”,目標是建立一個全球網絡,分享有關腦科學的所有數據,得到了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響應,當時筆者也曾為此歡欣鼓舞,為文介紹[17],但今天卻已無人再提及此事。 當然,今天我們有了云計算等新技術,條件已不能和當時同日而語,但問題并不完全在于技術困難。美國人類腦計劃為什么在紅火一陣之后會沉寂下去,究竟有些什么經驗教訓值得總結,需要認真反思。 以筆者管見,美國物理學家路克斯(Michael Roukes)所說的 “神經科學依然處于手工業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方”[18]不無道理,目前科學家的腦研究工具、實驗數據或計算數據格式五花八門,各有自己的一套,外人很難知道實驗條件的細節,很難共享也很難利用其他實驗室的原始數據,所以如何充分利用現有數據就成了個大問題。 此外,廣大的神經科學工作者和臨床醫生在沒有看到建立這樣的數據庫對自己有什么實在的好處以前,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數據提供給他人。也許對計劃內的人可以用經費作為杠桿迫使他們貢獻數據,或是一些得到國家大科學計劃(例如美國的人類連接組計劃)、億萬富翁資助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艾倫腦科學研究所)愿意公開其數據,但是和整個腦科學界相比,這畢竟還只是少量數據。HBP 是否會重蹈美國人類腦計劃的覆轍,還有待觀察。 另外,在腦的兩到三個層次之間通過建模和仿真發現隱藏在數據背后的規律是一回事(雖說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是要從最底部的微觀層次到最頂部的宏觀層次進行如此高度跨層次的建模和仿真,則是另一個問題。這絕不僅僅是提高計算機運算能力的問題。更何況,從科學發展史上來看,也并非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通過計算得到解決 —— 即使是最簡單的三體問題,也只是在作了極度簡化之后才能計算。所以以為只要加強計算機的計算速度和存儲容量就能在今后幾十年內解決腦研究的一切問題只不過是一種幻想[19]。
本文討論的是一些尚無定論的開放性問題,想在這樣一篇短文中充分展開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正是基于對這些問題的共同興趣,德國信息技術工程師和連續高科技創業者施拉根霍夫(Karl Schlagenhauf)博士和筆者通過電郵進行了長達 6 年的頻繁討論和爭辯,對相關問題做了仔細分析,最終經重新整理后結集出版[19]。其中既有共識,也有歧見。由于討論的都是這樣一些開放性問題,因此即使是我們的共識,也未必都成立,我們在此書中并不企圖告訴讀者結論,而是希望引起讀者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斷。由于我們在書中批評了許多人,當然這也就把我們自己放到了被他人批評的地位,本文當然就更是如此了。
-
芯片
+關注
關注
456文章
51155瀏覽量
426400 -
神經網絡
+關注
關注
42文章
4779瀏覽量
101059 -
數據
+關注
關注
8文章
7134瀏覽量
89424
原文標題:歐盟人腦項目:有錢有大計劃,就能做出基礎科學突破性成果嗎?
文章出處:【微信號:AI_era,微信公眾號:新智元】歡迎添加關注!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
發布評論請先 登錄
相關推薦
中科創達旗下MM Solutions推出突破性視頻降噪算法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2025年AI領域突破性技術

騰訊否認微信電商“遠大計劃”傳聞
Kimi發布視覺思考模型k1,展現卓越基礎科學能力
全新NVIDIA NIM微服務實現突破性進展
NVIDIA Research在ECCV 2024上展示多項創新成果
阿里云攜手中國科學院地化所發布首個月球專業大模型
蘋果獲得一項突破性智能戒指技術的專利
中國科學院青島生物能源所全固態鋰電池研究獲重大突破
人腦芯片是什么?植入人腦神經元的芯片能做什么?
里瑞通推出突破性晶片液冷技術
本源量子參與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青年科學家項目啟動會順利召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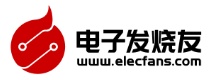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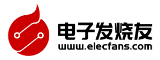


 歐盟人腦項目:有錢有大計劃,就能做出基礎科學突破性成果嗎?
歐盟人腦項目:有錢有大計劃,就能做出基礎科學突破性成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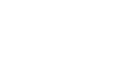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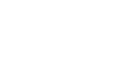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