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總是喜歡說我們‘轉型’——不要提‘轉型’!公司高管們都不同意用轉型”,一個月前,心直口快的華為終端董事長余承東用他一貫的簡單直接快速地打斷了本報記者關于“華為轉型挑戰”的追問,“因為‘轉型’會讓大家覺得今天干這個,明天想干那個,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南轅北轍。華為戰略是有持續性的,如果整天在改變,那就不是戰略了”。
華為堅持認為,在這輪由手機大戰引發的爭論中,外界并沒有讀懂華為。
不只是余承東,在本報持續一個月的采訪中,來自華為終端公司內部辯駁的聲音不斷。“‘華為是不是做互聯網’,這是一個偽命題”,8月2日,華為終端云業務部總裁黃冀針對近期質疑華為開發“天天聊”多種互聯網應用的嘗試時,強調說,“什么叫互聯網?現在是一個融合的時代了,蘋果是一個互聯網公司嗎?亞馬遜又是什么公司?互聯網、通信,都在融合過程中,華為要做的事情是要在一個融合的產業里邊怎樣找到自己的最佳的位置,我們認為最佳的位置是提供一個開放平臺和卓越體驗的終端,讓消費者能夠通過我的終端和平臺找到他最想要的應用,這是華為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一個個具體的互聯網應用業務。”
不僅如此,華為對手機業“PC化”有不同的認知。“智能機時代,我認為手機根本無法PC化”,華為終端CEO萬飚毫不掩飾的說,“PC化”的言論仍然停留在十年前“固定處理技術”時代的認知,“智能機代表的是無線網絡連接技術,有無數的軟件技術在里邊,還有對背后從‘管’(網絡)到‘端’(移動終端)的理解”,萬飚說,以CPU+微軟=PC的公式來推論IC+Android=手機,“這很荒謬,因為處理信息的復雜程度跟語音時代大不一樣了”。
毫無疑問,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華為,正在以手機為觸點,學習一種與外界溝通的語言,盡管這半年來,她一直被誤讀。
正如他的領軍人物余承東本人在微博上鮮明、獨樹一幟又飽受爭議的個人形象一樣,華為的異軍突起時常招至贊譽,也偶爾因為自己略顯笨拙的表現招致訕笑,這個B2B業務的優等生,在面向B2C品牌、渠道的塑造時,還像個初學者。“我們手機在進步,但是我們的好處總是表達不出來。”余承東坦陳。
那么,華為真實想法是什么?她應時代而生的手機業務能否、以及如何像她的母體那樣順利問鼎珠峰?華為終端公司依附于華為集團公司身上的整體戰略又是什么?
B2B與B2C的辯證法
英雄不問出身?——從華為手機開始面向最終用戶、走品牌之路開始,外界就從來沒有停止對其出身抱有的固執成見。
確實沒有理由不懷疑。在標準化程度很高的電信設備市場,華為面對僅僅是全球數百家運營商,其間的優質客戶僅有大約TOP50家,而全球移動用戶已經超過了50億。面對50家企業級用戶,與面對50億最終用戶,從需求的理解,到服務的手段,顯然大相徑庭。
事實上,即便是終端業務,華為的轉身也是從B2B開始的。華為終端副總裁童國棟回顧說,2004年華為終端的起家更像是給公司系統設備的銷售作陪襯,當時為了配合公司的3G戰略,華為開始被動地做起了手機。“3G網絡出來后,別人不給我們終端。類似下圍棋,因為缺少終端,它控制著你”,他回憶說,當時無線部門開始“忽悠”公司做手機——華為的終端業務因此而起。此后根據運營商的需求,華為將終端從手機延伸到了固定臺(固定式移動電話,適合山村等邊遠地區)、PHS(小靈通)等終端產品上。2005年,華為在歐洲市場取得關鍵突破后發現,3G網絡高速公路建好后,“路上沒有車跑,怎么辦?我們提了一個議案,找來3G殺手锏”,這個殺手锏就是后來給華為終端帶來豐厚利潤的移動數據卡,“我們把高速路拉到個人的用戶端,讓他無線連接,提供一個貓,華為首創的插口數據卡,讓人們解決最后一公里高速上網的問題”,這個方案不僅給華為帶來利潤,更為重要的是提升了運營商的ARPU值,大大提升了歐洲客戶對華為的信任。
但是,這段9年的“成就史”,此后成了華為終端拓展社會化渠道以及面向最終用戶時的包袱——顯而易見的是,華為至今仍有高達70%以上的手機通過運營商渠道銷售,運營商定制成為一種路徑依賴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組織的血液,要通過一場革命,通過改變“基因”來給組織上下洗腦嗎?
“必須從依賴工程師文化轉向消費者文化,但是在這個To B,還是To C的變化里,我們不想描述成一種革命性的,或者爬雪山過草地那樣悲壯的革命。”童國棟反問記者說,“為什么要把B2B和B2C對立起來呢?”
萬飚亦向記者指出一個顯著的事實——全球仍然有一半的手機通過運營商的渠道銷售,在一些發達市場這個比例甚至高達90%,“你會發現運營商資費政策的引導是全球手機銷售的引線,運營商給Iphone的補貼占(每部手機價值)51%,其它手機的補貼也達到40%”。他強調說,在手機這個市場上,有些人有一個誤區,“B2B與B2C并不矛盾”,他說,即便是蘋果,其商業上的成功也與運營商渠道密不可分,核心在于“運營商愿不愿意開放這個價格檔位給你?”
這才是華為手機的癥結所在——華為的智能機的首役主打“千元機”,這是華為的拿手菜,低成本、高性價比,幫助運營商快速爭取升級低價目標用戶群至3G業務,快速推高
運營商的3G滲透率——但是這樣的打法顯然難有高利潤率,更為嚴重的是,讓華為陷入“劃地為牢”的境地。“他(運營商)認為,你做可以,就做千元以下的,這正是我們的反思點,”童國棟說,“反過來說,其實我們在B2B運營商轉售市場,華為還有很大的改變空間。”
在華為看來,某種意義上,B2B與B2C殊途同歸,并且在B2C稍加用力,還能轉而曲線救國。“華為必須具備產品、品牌、渠道三大要素的融合,運營商才會開放高端給你”,萬舉例說,例如今年4月18日在中國首發的Ascend P1,這是首部華為從產品體驗、外觀設計、到品牌投放全方位轉身向外的產品,由于它在社會化渠道上的口碑,華為最終以2999的價位爭取到了運營商合約機的機會--“因為他看到你的市場表現了,然后才會給你開放”。
7月某日,余承東在他的辦公室向記者掀開了懸掛在墻上的一塊白幔,在那背后密密麻麻地擺放著華為近年來的眾多運營商定制機,他們有著青一色的呆板的外形,雖然其中不乏業績優良者,但是沒有一款因此與“HUAWEI”品牌連續起來,用余承東的話說,那幾乎是一個“白牌時代”——華為只做ODM,幕后英雄,只有運營商品牌,很少出現華為LOGO。
現在這塊白幔,就像是華為給那段“白牌”時代舉行的一個葬禮。“今年沃達豐的合約機已經開始打上華為的LOGO”——因為,另一個時代已經到來。
“硬”與“軟”的化學反應
今年5月,有外族基因,4年前被華為“挖角”出任華為互聯網業務部總裁朱波的離任一石擊起千層浪,媒體眾口一辭地說,“華為不具備互聯網基因,不具備成就互聯網的土壤。”
“這不是土壤的問題,是公司戰略的問題,”黃冀回應說,“我相信如果華為下定決心要進軍游戲、電商,也可能做得很好。但是華為的戰略不是做一個個具體的應用”,他認為,華為14萬員工、超過300億的銷售額、業務覆蓋端—管—云,“華為現在這么大的體量,而且已經是全球性的公司,我們的商業方向應該是打造一個開放的平臺和環境,跟業界一起來做。”
事實上,就在朱波離職前后,華為針對終端、及至終端公司與集團公司能力的對接做了一次大的組織調整:在消費者BG(華為三大業務BG,管道(運營商)BG,企業網,消費BG)之下成立了終端云業務部,與終端公司,華為終端芯片業務部作為平行的三大部門構成消費者BG主體。終端云的組成有三部分:一、原華為互聯網業務部;二、原華為軟件業務下與消費者相關的業務軟件;三、原終端公司從事軟件平臺、UI設計的原班人馬。該部門總裁由原華為軟件業務的負責人之一黃冀出任。
黃冀,1996年加入華為公司,歷任華為中央研究部干部部部長,南京研究所所長,印度研究所所長,電信軟件與核心網業務部Consumer業務產品線總裁。華為選擇在公司軟件能力構建上有著深厚積累的黃冀出任終端云這一決定“消費者體驗”成敗的關鍵部門總裁,而不是選擇一個具有外族基因的人出任總裁,其意圖富有深意。
華為EMT成員、輪值CEO徐直軍曾向本報記者如此描述這輪由云計算啟動的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和技術)業變革中的困惑:過去十年,華為和中國移動實施上馬了大量面向消費者的應用服務,神州行、動感地帶,139郵箱、彩鈴、閱讀基地、音樂基地……但最終因為運營商沒有及時的抓住消費終端的體驗而被蘋果等公司抄了后路,將收費站架到了電信的高速公路上。“短信、彩鈴、動感地帶都是萎縮的,歸根結底是因為電信運營商沒搞過互聯網運營。”
華為的困惑由此而生,“我們的軟件一直是給運營商業務作支撐的”,這決定了華為業務軟件的困境:首先,與運營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第二,如果繼續綁定在面向運營商的BG中,將無法形成面對消費者終端的能力,因為原來的業務軟件部門的需求定義僅來自于運營商。
這一困境,與華為軟件的能力并不匹配。2011年,華為軟件銷售額突破800億元,多年位居中國企業軟件收入NO.1,占華為整體銷售的1/3 強,其中針對消費者的業務軟件價值達到了將近300億元人民幣。“大家只知道我們是一個做硬件設備的公司,但實際上全球運營商面對消費者的增值業務有一半的平臺都是我們做的。”
黃冀告訴記者,在消費者BG之下成立終端云業務部,其意圖有二:一、激發華為的“軟實力”,加大軟能力投入,為華為終端提供差異化定位;二、作為公司“硬”與“軟”實力產生“化學反應”的關鍵點,為華為的“云戰略”打造一個能體現華為端—管—云能力協同的開放平臺和終端。
華為內部流行一個“水,管道,水龍頭”的形象比喻,“要讓全世界的人能夠像用水,用電一樣享受信息與運營服務”——這是一個偉大目標。事實上,這就是“云時代”對一個普通人的意義本質——人們從以PC為核心的網絡時代步入以手機等各類移動終端為中心的時代,所謂“體驗”的差別就在于,人們從 OFFICE等技術語言障礙中完全抽離出來,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自由人,對語音、信息、數據、計算等各類信息的獲取,就像打開水龍頭那樣簡單易行。
華為的水龍頭即是華為終端業務,它存在的意義不只是讓華為窮盡20年創業積累下來的水——數據中心、業務云,獲得一個釋放的端口;在云的時代,華為更希望通過“端”的能力升級,提高管道和華為云的價值,有人評價說,“網絡接到每個個人、家庭,管道里跑出來很可能不只是水,而是各種鮮活的應用和體驗,有華為自己做的,也有別人做的,這就是所謂的開放平臺”——此為華為的整體謀略。
文化的變與不變
“余承東這個人,心無城府,狼性十足。”一位接近華為總裁任正非的人士如是評價說,這多少概括了華為公司對終端的期待。
華為創業20年,在2011年之后再次步入一個十字路口:向左走,電信設備市場經歷了若干輪大浪淘沙之后,在余下少數的競爭者的同時,市場的天花板已經到來;向右走,通往電信云與互聯網云的融合之路,新的技術革命似乎再次把ICT業者的競爭起跑線重新拉平,但機會與挑戰同在。猛獸與羚羊、野兔一起賽跑,沖進跑道的有電信設備商、PC廠商、軟件服務商、互聯網企業、手機廠商……前路荊棘重生。
華為內部固執地認為,這輪生與死的大考面前,華為核心價值觀和文化基因不需要改變。比如,在執行力上,“產品、研發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由一線呼喚炮火”的企業文化,“這些從來都不需要改變”,萬飚說,不同的是,就終端業務而言,“客戶”的內涵已經發生改變,從過去的運營商,延伸到最終消費者。
相比余承東,鮮少公開露面的萬飚,同樣出自身自華為無線產品部門,他對手機各項技術指標、對宣傳華為競爭能力的狂熱并不亞于余承東本人。萬飚與領導終端云的黃冀、以及更為低調、從未露面的終端芯片業務部總裁丘鋼(來自海思半導體公司,根據公開資料海思連續多年位于中國半導體銷售排名首位),三人一起,與消費者BG的CEO余承東一起,是華為終端業務的“夢之隊”。某種意義上,前三人是“收斂版的余承東”,他們共通的特質是,浸淫華為多年,文化基因深入骨髓,比如業務聚焦,比如對夢和愿景的堅持,再比如對技術和積淀的崇拜和狂熱。
由此四人擔綱華為向最終消費者的轉型,體現了華為演進的思路:通過組織的適配,以終端公司為核心,輔助以軟件、芯片兩大優勢能力為其兩翼,形成終端的協同效應。”
“如果是在過去的網絡計算時代,我們也不敢去干消費者的業務。”徐直軍說,是時代和技術變革給了華為機會,因為在云計算模式下,ICT的商業模式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種變化把世界拉平了,也把華為放置在一個新的起跑線上,“能不能走出一條路來,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至于華為終端廣被詬病的品牌和渠道能力,華為內部認為,品牌之路有三步論,先要有強大的產品,其次才是解答“我是誰”的問題,而后是建立“我與消費者的關系”。就當前的華為而言,華為能力的構建仍在前兩步階段,如何把產品品質與體驗樹立起來,是品牌的核心和基點。正如余承東不厭其煩地在其微博中對各項技術指標所表現的狂熱一樣,放在華為手機未來更漫長的競爭道路上,他當前的孜孜不倦,一點都不過分。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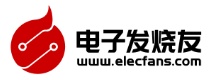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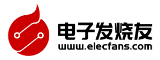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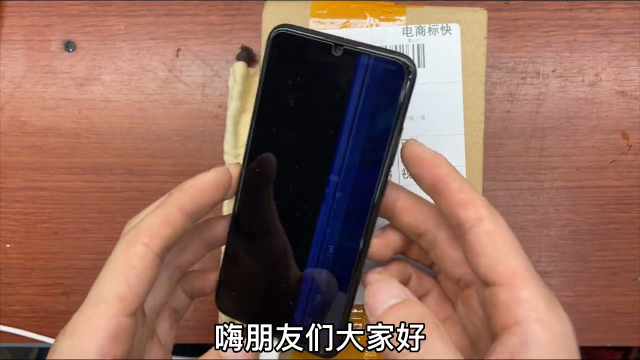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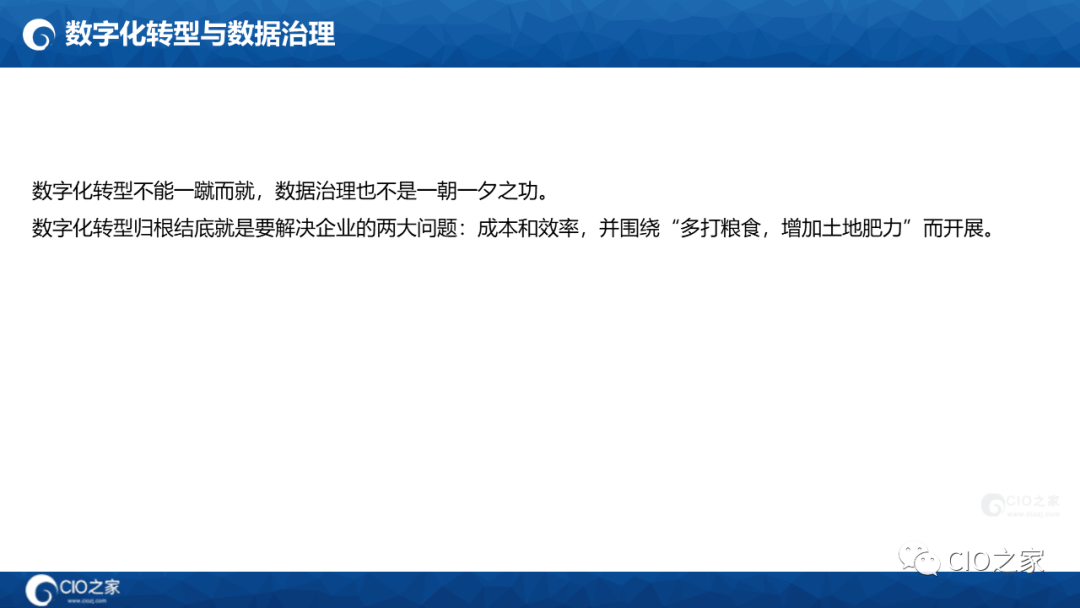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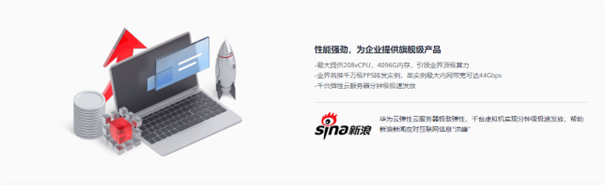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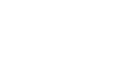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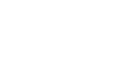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