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個離開西雅圖的人,請關燈吧。”
在 20 世紀 70 年代,位于西雅圖的飛機制造商波音公司深陷泥潭。文章開頭為一塊廣告牌的標示語,這塊廣告牌立在前往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的路上,向旅客們致意,至今已有半個世紀。
但西雅圖最終沒有步底特律后塵。在 20 世紀末,在西雅圖長大的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將原名 Micro-Soft 的軟件公司改了名,從新墨西哥州搬回西雅圖,在華盛頓湖對面的一個郊區建立了公司。
如果蓋茨和艾倫決定在阿爾伯克基建立微軟公司,西雅圖這座城市后來會怎樣呢?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但西雅圖的復蘇更多地依賴于運氣,而不是人們通常愿意承認的其它原因。
我們喜歡想出一些理由,以解釋為什么會發生重大變化,或者說如何發生巨大轉變。畢竟,我們聽到了關于創新文化或地理優勢的堂皇敘述。但其實,在重塑西雅圖經濟命運的過程中,意外發揮了巨大作用。
西雅圖等地的歷史很大程度上由“住在哪”等隨機個人決定推動,或者由 2008 年金融危機等“黑天鵝”事件推動,對這些因素的依賴程度,不亞于命中注定。
這些事件所提供的預測未來之法可能不太令人滿意,這些當然更多是一堆錯綜復雜的理由,而不是專業未來學家想說服人相信的事情,但這些方法不僅對于西雅圖來說是準確的,對硅谷也是如此。
關于是什么成就了硅谷的獨特,一直存在許多爭論。而“硅谷”這個名字是科技記者唐·霍夫勒在 1971 年所取,恰好在同一年,“請關燈”廣告牌出現在了西雅圖。
從那時起,無論硅谷是出于何種原因一直保持世界上最主要的技術創新中心地位,硅谷都顯然扎根于一系列偶然事件。
首先,威廉·肖克利決定離開貝爾實驗室,由于想離年邁的母親近一些,肖克利在舊金山灣區帕洛阿爾托開辦半導體公司。
幾年后,美國司法部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提起反壟斷訴訟,強制免費許可了該公司的集成電路技術。晶體管和計算機因此爆炸式發展,一波又一波的變革隨之而來。
盡管硅谷幾乎像信宗教一樣相信創新,相對來說,硅谷幾乎不是由戲劇性的大概念支撐。這些概念包括道格·恩格爾巴特的超文本和鼠標,艾倫·凱的 Dynabook(筆記本電腦的前身),馬克·韋瑟的“普適計算”,都催生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硅谷其實是在產品工程方面蓬勃發展,并開始擅長發現有利可圖的新創意。
芯片制造商英偉達的首席執行官黃仁勛告訴我:“每當有一個新想法,硅谷便敞開懷抱。好想法必須得等,而且不是每天都有。”
由于硅谷有實力的風險投資業,及硅谷為新創公司提供資金的效率,對好想法的關注度更是上了好幾層樓。在 2019 年,舊金山灣區的風險投資總額超過 500 億美元,遠遠超過了美國其它地區的總額。
所有這些都點明了一場轉型,即舊金山灣區從制造業轉向硬件工程和軟件設計。如英偉達創立之初,是為視頻游戲設計圖形處理器,后來果斷轉向機器學習應用。
但是,好想法并不僅僅是罕見,還是令人牙癢癢得難預料。硅谷的大神都沒料到有網絡、搜索引擎和機器學習。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幾十年來計算能力加快發展,計算成本不斷下降,意想不到的新事情便成為可能。每一代新芯片一出,創新便像上了發條一樣不斷涌現:臺式個人電腦、筆記本電腦、數字音頻和視頻、智能手機、物聯網。
自 2013 年以來,硅谷的主要信條摩爾定律就開始搖搖欲墜,現在,意外之喜可能更難發生了。事實上,至少在一個重大方面上,創新已經完全停頓。單個晶體管的成本曾經以與晶體管密度增長相同的指數速度下降,但在超過三代的芯片制造中,沒有任何改變。
創造了“摩爾定律”這一術語的物理學家卡弗·米德幾年前告訴我:“我們基本是搭上了順風車。真的很瘋狂,但這就是回報。”但是現在,搭順風車之旅結束了。只有人類的聰明才智,才會帶來重大技術進步。這就意味著,硅谷是時候要么采取行動,要么毀滅。
在知名公司紛紛退出之際,尤其值得牢記意外二字。就在 2020 年 12 月,惠普和甲骨文宣布將總部遷至得克薩斯州,特斯拉也表示可能會效仿。這些公司的舉動,引發了新一輪關于硅谷是否已經失去魅力的擔憂和猜測。
但這并不是人們第一次這么發問。在過去,有些時候進展似乎滯后,直到一些突破洶涌而來。這些突破,似乎完全來自硅谷。
例如,到了 2006 年,人們感覺硅谷的創新似乎正在減少,而諾基亞和 Psion 等歐洲公司首先在移動硬件上取得進步。但在 2007 年,史蒂夫?喬布斯推出了 iPhone,顛覆了蘋果公司兩大最失敗的產品:牛頓掌上電腦和 General Magic 個人通訊工具。幾乎在一夜之間,硅谷重新主導全球信息技術創新。
早在淘金熱時期,北加利福尼亞就一直盛衰輪回。我在帕洛阿爾托長大,聽說過美國宇航局艾姆斯研究實驗室和洛克希德導彈與航天公司大規模裁員后,大批工程師離開了。
在互聯網泡沫破碎之后,我在一次會議上遇到一位創業多年的人,想起來已經好幾年沒有見到他了,這時我又想起了曾聽聞過的裁員事件。
我問他:“你去哪兒了?”他回答說,自己之前離開加州,與家人同住,但事情好轉了,現在又回來了。
這并不是說硅谷注定會生存下來。盡管現在投資和風險資本風頭正勁,但除了半導體行業停滯之外,還有新的不確定性因素。
一個是關于引進人才的能力。在很多方面,硅谷存在都歸功于上世紀 70 年代因芯片發展而首次顯現的神秘感,這創造了一種磁力,源源不斷地吸引著世界各地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事實上,這可能是理解硅谷與其他創新中心區別之處的關鍵。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我在 Byte 雜志擔任技術編輯,有一次偶然間發現了這一點。桑尼韋爾當地的一位硬件設計師帶我去了一家印度面包店,里面滿是穿著紗麗的婦女和她們的工程師丈夫。
磁盤驅動器行業迅速增長,這些關鍵腦力勞動者都到了硅谷。在當時,內存十兆的硬盤可是件大事!歐洲人、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也來了,帶來了知識和企業家精神。不到十年時間,在硅谷,我們可以開車從一個街區到另一個街區,看到用不同語言寫的商店招牌和廣告牌。
然而,現在美國反移民聲勢浩大,即使在拜登政府治下,對外國技術工人和企業家還會有新的壁壘,那么硅谷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將遭扼殺。
不確定性的另一個原因是,下一個重大技術轉移尚不明確。過去十年,摩爾定律的步伐放緩,硅谷在最近兩代創新之間進行了過渡,從社交媒體平臺到基于機器學習的軟件和服務。風險投資開始轉向,由于投資者紛紛涌入機器學習創業公司,社交媒體融資在 2012 年達到頂峰,到 2016 年幾乎降至零。
然而,關于“下一大事件”會是什么,或者什么時候會來,現在還沒有達成共識。未來主義者認為,AR 可能會觸發下一輪投資潮。一些樂觀主義者認為,整個亞洲平板顯示器行業都處于危險之中。
或者,軟件和生物學最終會融合,畢竟,最近 mRNA 新冠疫苗的成功,已經大大推動了合成生物學。又或許,量子計算將商業化,大幅降低谷歌數據中心的成本。或者還可以考慮,蘋果汽車若像 iPhone 一樣成功,能有什么影響。
但是,同樣有可能出現創新陷入長期枯竭狀態。西雅圖曾因過度依賴波音而陷入困境,硅谷也可能會面臨相似困境。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可能會成為硅谷的激烈競爭對手。硅谷也曾經擔心,日本會是如此角色。
當然,也有可能真正對下一個技術平臺構成威脅的,首先會出現在上海、深圳、或者北京。任何一個參觀過北京中關村的人都會發現,中關村與硅谷在人才和資本集中方面有相似之處。
話雖如此,但與意外、或者與硅谷對賭,似乎仍不明智。經常有人預測硅谷即將消亡,但向來都是短視的。
這一教訓我也親身領教過。我曾參與撰寫于 1985 年出版的《高科技的高成本》一書,該書認為,增長造成的環境和勞動力成本,將很快限制硅谷的擴張。我的合著者是萊尼·西格爾,他后來成為山景城的市長,也就是現在谷歌總部所在地。
原文標題:西雅圖曾因過度依賴波音而陷入困境,硅谷是否會重蹈覆轍?
文章出處:【微信公眾號:DeepTech深科技】歡迎添加關注!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
責任編輯:haq
-
集成電路
+關注
關注
5391文章
11617瀏覽量
362826 -
半導體
+關注
關注
334文章
27687瀏覽量
221510 -
硅谷
+關注
關注
1文章
123瀏覽量
16567
原文標題:西雅圖曾因過度依賴波音而陷入困境,硅谷是否會重蹈覆轍?
文章出處:【微信號:deeptechchina,微信公眾號:deeptechchina】歡迎添加關注!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
發布評論請先 登錄
相關推薦
2025中國(華東)智能家居技術創新研討會

國科微榮獲技術創新企業獎
飛凌嵌入式獲批建設「河北省嵌入式計算機控制系統技術創新中心」

淺談天合光能技術創新與戰略布局
節能回饋式負載技術創新與發展
飛凌嵌入式技術創新日(深圳站)精彩回顧
2024磁集成技術創新與應用研討會

天馬斬獲“DIC國際顯示技術創新大獎”
韓美將在硅谷設立AI芯片創新中心
孫東: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地位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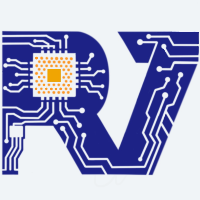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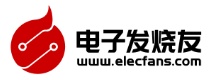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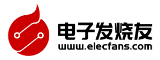


 保持世界上最主要的技術創新中心地位的硅谷是否會重蹈覆轍?
保持世界上最主要的技術創新中心地位的硅谷是否會重蹈覆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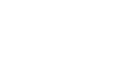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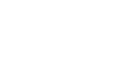





評論